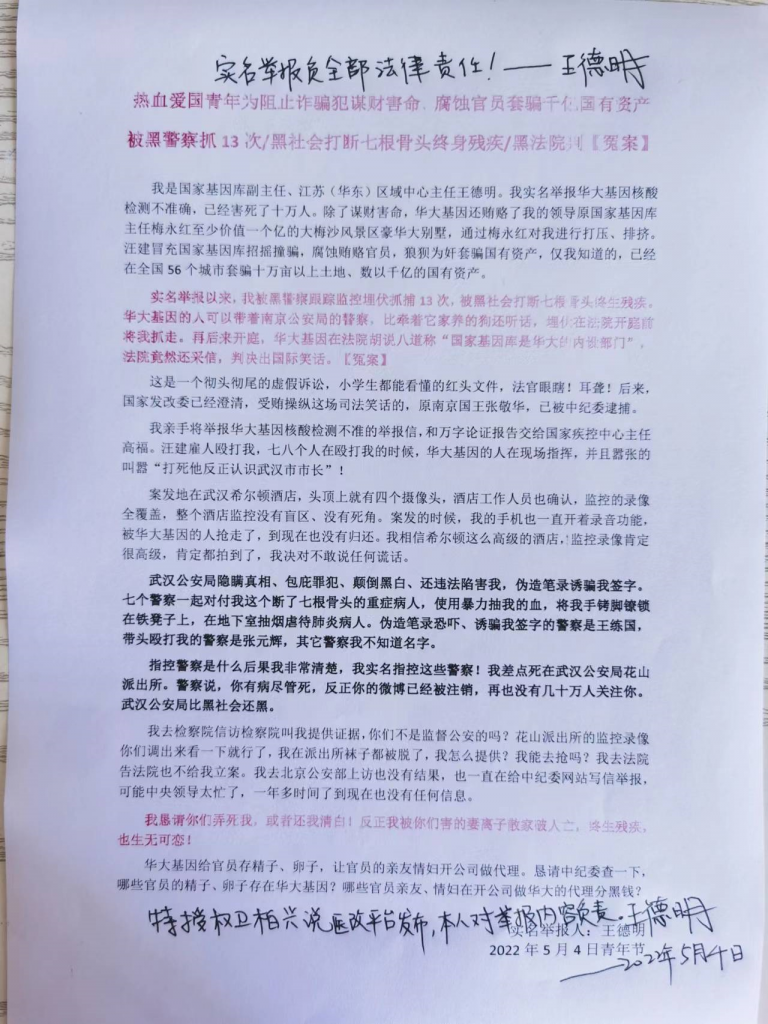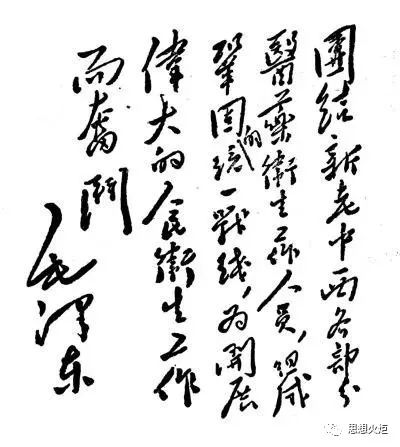唐山打人事件反思:是谁消灭了见义勇为者?
[枪打出头鸟,就是为了消解民众中的见义勇为精神。因为见义勇为,是黑社会的大敌。倘若人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黑恶势力将没有生存空间。]
唐山打人的那段视频,真正让我脊背发凉的是:那群骚扰受阻的暴徒,首先重度施暴的对象是那位出手相助的勇敢女性,整段视频中,他们几乎精准打击了每一个试图提供帮助的女性(这其中甚至有“误伤”)。并且,他们甚至对帮助帮助的女性也毫不犹豫的挥去拳头,似乎在他们眼里,帮助者比原本他们想要施暴的对象更讨厌、更可恶,从而更需要穷凶极恶般的打击。
对帮助/声援/支持者更为优先,更加剧烈的攻击,你我在现实中对之其实并不鲜见。这种对于帮助者的格外憎恶不仅涉及犯罪心理学,更攸关权力技术学,不得不说,这群暴徒几乎精准、狡黠的掌握了权力/暴力的得以最大化的要诀——消灭她的朋友。
施米特说,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友,但以施米特的口径,他似乎更想说的是:政治的本质在于挑出敌人。正基于此,一个不那么暴戾的版本也可以推论得出:政治的本质在于找到朋友,这也正是德里达《友爱政治学》的立论基础。然而,在解构之路上战无不胜的德里达却最终却折戟于此,他和我们都低估了“恶”的烈度,真正的权力/暴力不在于以你为敌,而在于——让你无友。
消灭友谊、割断情感,隔绝联系,让个体孤零零的面对权力和暴力,这正是他们的目的。开除社会、毁掉人际,分化关系,让个体赤身裸体的面对丛林和野兽,这正是他们的目的。所以,他们憎恶朋友高于敌人,嫉恨帮助高于反抗。因为他们知道,当所有人都开始驯顺的学会服从而冷眼旁观,当所有人都开始深感无力而选择放弃,人就自动降格为自私自利,进而贪图安逸,最终是虚弱无能的费拉。由此,他们就迎来了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,一个没有对手和敌人的世界,一个“人”作为“物”任其摆布的世界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阿甘本在疫情期间发出他最深刻同时也是最不为人理解的担忧:人不能失去人的联系。一旦人们失去互相照面的脸、失去了友谊、失去了爱情、那最终失去的,就是“人”。而这一失去恰恰换不来安全,相反,它最终损害的正是安全本身。在埃利亚斯•卡内蒂的代表作《群众与权力》中,他告诉我们:人只有在群众中,陌生的恐惧才得以被逆转,正是在群众中,人才有力。而人唯有有力,她才能呼吸。阿甘本曾引用海德格尔说:“一旦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,‘物’本身即是可怕”,那么依阿甘本的逻辑,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结论:一旦失去了与人的联系,“人”本身即是恐惧。
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
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
《论语》的开篇其实是一段恐怖故事,我希望那最后,同时也是悲哀的结局——“人不知”,永远不要到来。
为此,就像我在2月24号说过的,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也“无需惊讶周遭发生的一切,恰恰是这些打破常态的例外才让真正和本就存在的一切清晰起来。它让我们看到伙伴,找到朋友,确认彼此的鼻息,相互的友谊,而这些,正是作为人的我们得以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下去的理由”。
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以敌人的方式被定义,我更愿意相信,世界的意义在于朋友,在于我爱的人,在于爱我的人,但是,如果有人试图剥夺ta们,我们将奋不顾身。
来自微bo 古门门 6月11日